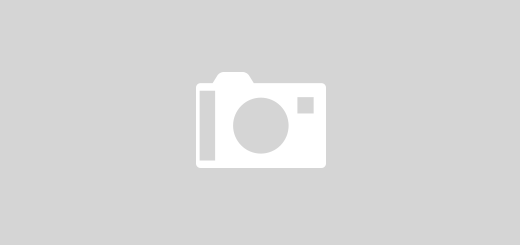我 的 父 亲
我的父亲
父亲已故正十年,儿女思念常祭奠。
挥笔写下几千字,再展生平重客观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是一个较为标准的男子汉。他的爱好十分广泛。听玩意、哼川剧、打大贰、讲<<三国>>、说<<聊斋>>、评<<水浒>>、谈典故等。可以说是样样来劲。年轻时曾与我老表家的高材生(是个老辈子、是某高中的高级语文教师)探讨<<古文观止>>上的文章,常常是废寝忘食。一打开话题就是半天。什么“狡兔死、良弓藏……”。等古句,几乎成了父亲的口头禅。
我父亲相当爱交朋友,在哪儿都有一帮铁哥们,我曾记的、在我二十二岁那年,上宜宾师范时,他的好朋友杨叔叔不仅用车从泸州送我到校,而且是一路上包吃包玩,到了宜宾后还要办我的招待。真是热情周到。这样的事情,父亲的其它好友也是如此。这都是因他平时对人大方豪爽的缘故。父亲给邻里间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错,从未见到他与那家闹过矛盾。在外人的眼里,他是个既健谈又乐于助人的人。他给自己弟妹的关系都很好,从未红过脸。他处事的原则是,家外嘻嘻哈哈和为贵。家里说一不二严管理。凡是自己孩子与别的孩子发生了不愉快,首先是自己的人,先挨五十大板再说。这就是我父亲解决问题的初始化法。父亲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他在家里的脾气十分爆燥,常常因一点点小事就爆跳如雷。有时、父亲下班回来,我姨妈没及时煮好饭,他就发脾气骂人,这时,我哥俩最好离他远点为好。有些时候、饭菜不合他的口味,他也要冒火、坛坛罐罐、锅盆碗盏,不小心损坏了,他要冒火。小孩玩耍时,比他晚回家几分钟、他要冒火。他是个爱冒火的人。
父亲的火都在家里冒。而且主要是在孩子身上起火,于是、打孩子就成了我们这个家的家常便饭,父亲打起孩子来相当凶狠。小时候、我清楚地记的,在我们那不足十二平米小屋内的床上,常常露出几块又宽又厚的篮竹板,有些时候打手掌不解气就打屁股,打屁股不解气就全身打。他的气很多,有时、我们真不知到他从哪里冒出这么多气来。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多家庭都有整套的办法来收拾孩子,有的用叉头细条打、有的叫孩子跪碳渣、跪扫帚、有的父母对孩子用常备的黄荆棍来抽打。听说“黄荆棍下出好人”这句话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看来用黄荆棍打人是父母的一片苦心。而我们家,父亲管教孩子很有特色,打人的工具也十分考究。用的是又大又结实的老篮竹片,这种材料,在大山里才好找,它的特点是,用得上力、不易断、经久耐用,如果搞一个质量评比,我父亲的老篮竹片很具有竞争实力。打法是我父亲最大的亮点,他冒火时,手持竹片,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是发出强硬地声喑,叫孩子“跪下”!接着他就抽烟。如果你跪的姿态出问题,他就会无须警告地给你一下。这是很重的打法,完全是随意性的,没有精准的位置。如果你跪的标准,那你就等他把烟抽完后乖乖地伸出手来,只要亮开手掌就行。至于打多少?那就要看前次被打的是多少。只要能翻一翻就可以了。关键是你自己还得把帐目记好,否则、还会加倍受苦。就是这样好的竹片,常常因父亲用力过猛,打断了不少。家里都换了好几批。那个年代、各家的娃娃都多,四五个一家的,不在少数,父母整天为生活奔波,国家实行的是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的上班制,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弄得十分疲惫,再加上大家生活的质量都很差,根本就没有心思和精力来培养自己孩子。于是、众多家庭就用简单而粗暴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父亲晚年的个性,象是一根退了火的钢筋。软绵绵地几乎失去了力度,与他年轻时相比,完全是判若两人。因而,进入九十年代的我们家,变得十分和谐。
我真正认识我的父亲,是在他安渡晚年的时候,在九十年代初,每当闲下来时,我总要在他的身边聆听老人家讲述昨天的故事。听多了,渐渐地认识了我的父亲。我认为、父亲的个性,是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导致,更是那纷繁复杂的时势变迁所形成。
我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个较为富有的家庭。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读过私塾、进过泸州有名的商校(原地址在水井沟)抗战时期。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由蒋经国领到的中国抗日救国青年军,每当提起此事时,父亲会很精神地说:“那时、我们在泸州大教堂接受蒋介石的训导时。小伙子们个个都站得毕挺!毕挺!!”。我笑着对老人家说:“就是不敢拉出去,真刀真枪地给日本人干!“瞎说!”我们队伍里个个是热血青年,只要上头一声令下,我们立刻开赴前线抗日”!父亲这样回应了我的提问。一九四五年。正当四川的青年军要开赴前线时,抗战胜利了,‘青年军’也随之结束其史命。我父亲作为培养的重点对象之一,被派到泸县‘河丰乡’当乡队副(相当于乡武装部长)老人谈起往事,有历历在目的印象。他说:“每当自己回通滩老家时,总是骑着一匹大白马,后面跟着十几号扛枪的人,好威风!”我笑着说:“你们国民党的官就是这样,小官都这样。父亲听我说后,反思了一下,他补充说道:“那时年轻,年轻人总喜欢出风头,讲排场”。“那道是”,我正面回应了一下。看来、人老了,火气少了好多。
四九年秋、国民党在三大战略失败后,气数也尽。解放军南下的队伍,势如破竹。认清形势,作出选择。是我父亲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又是必须做的事情。识时务者为俊杰,马上交出队伍。保全性命要紧,于是、他作出了非常明智的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当机立断地把自己的队伍交给了共产党。结果、我父亲不但没受处分,还当上了剿匪征粮队的副队长(正队长是解放军里当官的)这一年他过得很充实,整天忙碌于剿匪的事。据他回忆说:“‘老山上’、‘黄天树’、‘么子岩’、‘排峰山’等,都是我们取得战绩的地方。部队在剿匪的同时又开展了一系列对土匪的策反工作。平息匪患的工作进展十分迅速。那些顽匪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在这年的年末,土匪头子带信到我父亲的家里,限他三天之内离开征粮队,否则杀死家人。父亲语气沉重地对我说道:“当时你母亲得到纸条后,一时急得不知如何办才好,但,很快我们俩就作出了决定。决定当晚动身,办法是,由你母亲带着你那未满周岁的哥哥从通滩后场的河边上小船。然后乘船到泸州,暂住到大婆在‘小白门’的家中。就这样、我们家就来到了泸州,从此、成了城里人。父亲继续战斗在他那熟习的山区。,
五十年代初。剿匪工作完成后,共产党为了巩固政权建设、把各项政治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我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曾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小官;关键是在执政期间,在辖区内,自己亲自同意处决了一个人。(此人犯了不少事,当时是影响很大、很难抓获,我父亲带队布控几天才得手,最后在各方的压力下,才下了处决该人的决心)。政权易帜后,按当时的政策,我的父亲就是血案在身,再加上是国民政府时期当官的,被枪毙是早迟而已。怎么办?他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地问自己。最后、我父亲采取了自己一生中最大胆而又最不光彩的行动。出逃!逃命是当时这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的唯一选择。
那天夜里,趁人不备,悄悄地溜出了单位的大门,箭似般地跑进了那无边的黑夜。谁也不知、谁也不晓。此时、就是自己的妻儿,也未能看到他出逃的身影。也许、这时他的妻儿正进入了梦香……。
父亲慌张地跑出后,一夜兼程,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住在‘四面山’的我姨妈家。他在‘四面山’躲藏了两个月。据他后来回忆说:“在你姨妈家白天不出门,晚上早关门,而且是把姓名都改了。一旦有人问起姓来,就以曾勤志的名字对答(原名叫曾明志)。说是一个走亲访友的亲戚就是。就这样,我姨妈姨爹帮着我父亲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那段时间,我母亲带着我那未满周岁的大哥没少吃苦。
父亲跑后,母亲被临时关在监狱里,据母亲回想说:当时我确实不知道你父亲的下落。“随便他们怎样问,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当时心想,他一定是就近躲藏起来了,由于我整天把孩子弄得呱呱叫,看管很心烦,再加上又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最后只好把我们母子放了”。
命当有去处,生逢不绝路。五十年代中期,朝鲜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以曾勤志的假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东北的‘丹东’集训了几个月后,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父亲是晚年时,手拿着入朝纪念章给我谈起那段往事的。“当时、我们部队进入到‘朝鲜’后,连续好几天夜里行军,白天睡觉。美国的飞机根本炸不着我们”。我插话说:你是混进队伍的,睡得安稳吗?“没想那么多”,这是我父亲的回答。他还说:“我在连里是文书,在众多的文盲面前,我是人才。连里只要是动笔的事,我是首选的笔杆子,情书都帮别人写得不少”。的确、当时是相当缺有文化的人,否则、父亲肯定混不进去,更不说是二次被选入朝,还是全连唯一。他跟连长的关系好,很可能是经常给连长写情书所建立起来的感情。拿他的话来说,“叫做形影不离”。
我父亲因有文化而两次入朝,同时又是因有文化救了自己。回到祖国后,部队开始整治,队伍里搞政治运动,政策性很强。父亲借助自己能说能写的水平,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他把自己的想法、观点、做法、经历等方面的内容,本着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全盘写出。上面根椐他提供的情况,派了两名政工干部到泸州进行了情况核实。结论很明确:“情况属实”。结果是、历史问题不再追纠。退伍回地方,责成地方安排工作。
我父亲回来后,虽说没享受到转业军人的待遇,但是、国家给他安排了三次工作。第一次、是安排教书,被拒之。理由是,“我没有耐心,要打孩子”。的确他有自知之明。我们兄弟俩对此深有体会。第二次、是到重庆钢厂上班,这一次他在厂里呆了一年就回来了,理由是、不自由,会多。第三次,他选择了当搬运工,这一次他最满意,一干就是几十年。理由是,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吃的口粮多(45斤一月,听说父亲当年一口气吃下过十个高级饼子),挣钱也相对多些,又自由。这下他总算有了一个归宿。
文革期间,我哥因父亲的事,参军时,没过政审关,没参成。我因他老人家的事,没入成团。那时、象我们这样的受害者很多。中国的‘成份论’害了不少进步青年。那时,我的父亲象看破红尘似的。哪派他都不参加,别人把钢钎立在他面前,他都无所为,就这样、凡是政治问题他都不过问。
追忆我父亲的昨天,我感慨万千。他是个书生,却没有书生的酸气。他是个军人,有军人的丰度和气质,却没有军人的福气。我的父亲晚年很快乐,弟妹之间很和睦。他对家庭充满着爱和期待,他是九九年离开人世的,他的一生,给我们家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并激励着我们后人勇敢地面对生活。面对人生。走出自己更加坚实地路。
最后、我将用下面的八句话来结束本文!
我的父亲
历经磨难人生路,倍感艰辛长吃苦。
出征年年多风雨,道上天天需识途。
进退得知方向好,生死关头敢作主。
终归有幸把家还,阵阵心酸好倾诉。
二00九年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