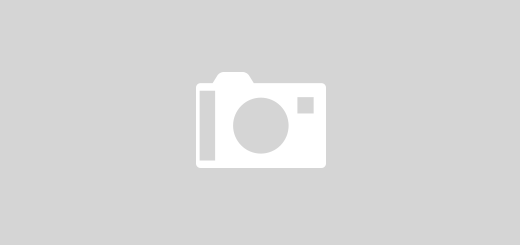一段沉寂的记忆
——记我的老师耿洪恩先生
耿洪恩先生是我的老师。是那种我们坐在讲台下面他则拿着教鞭走动在讲台上殷殷教导我们念书的老师,不是现在在一些场合人们无法“冠称”却又要客套地去应酬叫叫的那种“老师”。我们受教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因为我们而在历史中留下的一些特定的词汇,如“老三届”、“老知青”、“红卫兵”等等,在现今的许多人看来,几乎就是“无能”的代称。但虽然实在说我们所学的东西的确不多,而好像我们这一代中痛悔于那个时代的虽有倒也不是很多。据1999年底湖南卫视举办的“‘老三届’恳谈会”透出的信息说,这一代人中很多至今无悔于那个时代,当然也无悔于他们的人生。
至于那时候我们所学东西的多寡,倒实在是怪不得老师的,因为,据我所知,那时候我们老师教学的认真态度与今相比,是绝无差别的。若要硬说差别倒也有一例:那时候我因一时未认真听课,曾被罚站了一堂课,现在有一所学校的一位老师则改罚他的学生为其装上热水罐。
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最尊崇的是“天地国亲师”。“师”即位列于最“尊崇”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学生心里的地位,便绝非所谓时代“动乱”就可以轻易撼动的。所以,那时候—我这里说的是1968年,还是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那时候,我们已从先前的背着书包上学转为戴起袖章“造反”了,但从心里对于老师的敬—在那种少不更事的年龄里叫敬重似乎不如叫敬畏贴切—仍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譬如散文大家余秋雨罢,据说他在很有名气之后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仍还是情不自禁地要站起来去听。这确也可以推而广之地看成是学生对老师敬重的一种真情写照。
所以,那时候虽然“造反”了,我们对于老师的话或文章,仍免不了还是要去看去听。
1968年,我的老师耿洪恩先生以墙报的形式,写了一篇词。这篇词的主题是反对当时的“苏修”入侵珍宝岛的,曾被我抄在一张卡片上,十分可惜的是终因年代太久远,竟散失了,依稀记住的下半阕是:“壮志撼云天,仇恨频添。红旗如海没王冠,安定绿洲何处是?处处火山。”
老师的词就贴在那时工人广场路边的墙上。这篇词给我的印象极深,让我认识了诗,认识了艺术,认识了艺术的感染力,以至于仅仅靠此便时时勾起我对校园生活的怀念:窗明几净的教室。整齐参天的大树。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槐花和一朵朵紫莹莹的桐花。那确是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而我的喜文和习文的兴趣,也许竟就是因了这篇词的启蒙。现在仔细想来,这篇词除了大气磅礴之外,能让我记忆犹新的,大概便是其中的“情”吧。
但这词中饱含的情又绝非现时流行的吟花诵草或无病呻吟的情,而是一种关注,唱和时代的“大情”。
我的老师耿洪恩先生虽非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或宇内驰名的大人物,但也绝非那种只靠嗡嗡嘤嘤或只会附庸风雅的文人。据他个人说,他一生执教42年,业在教育;早年习作新诗,后又改写传统诗词。他说的业在教育,我当然可以算感受最深。在学校里,他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教我们,读书、作文、做人。即便走进了社会,他已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县诗词学会会长了,时常要坐到县文联的会议桌边议事了,对于我这个承蒙几任文联领导抬爱而被时时招来打打工的他的学生,仍总是要殷殷地告诫几句:“写诗作文要有真情,要出新,最重要的是反映人民的心声。”他把对后辈的教育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责任贯彻了一生。
至于他说的“改作传统诗词”,那就更有许多作品作为佐证。他创作的《七律•夜读偶感》、《七律•雪》、《一剪梅•酒歌》、《七律•老人节》等诗词分别被选入《当代中华诗词选》、《江南诗词选》等选集。他创作的《水调歌头•献给黄河母亲》获1988年“黄河碑林诗书画印”国际征稿活动的优秀作品奖,《一剪梅•酒歌》获“宝丰酒国际诗书大展”优秀作品奖,《七律•春到大别山》获1989年首届“苏东坡国际书画大联赛”优秀作品奖。他创作的《蝶恋花•教师节》更是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1万多件投稿中荣夺“镜泊湖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此外,他还有诸多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的报刊,结集有《求索庐诗稿》诗集一部。
他执教,又做文。但不管名气的大小与否,也不管执教做文或为人的是非如何,其实他的一生都很完整。他执教认真严谨,令我辈似的弟子们至今记忆犹新。他做文也在以文教人,绝不拿附庸之作去误世误人。便是我所读不多的那些作品里,即如:“老蚕欲吐回春索,绾住西霞护晓阳”的句子,细品起来亦不免让人肃然起敬:为护“晓阳”宁以“老蚕”之丝去“绾住西霞”,这又是何等的胸襟?他做人,不以“名”向人,不以文骄人,不以“利”取成,不论达官显贵或芸芸众生,在他的眼中皆一视同仁。而所有这些用他自己的诗句表达出来,便成了:“浮云富贵非余愿,万里征程唱大风。”
无论有名无名,无论执教为文做人,他都在把关注社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更何况,他的心中,他的诗文中,始终记住的还是人民!
现在,到了这篇短文该收手的时候了,所以我想我也该来说说我为何会始终记住老师的那篇词的原因了。
前些年,文艺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应以表现自我为根本。这当然是一场无结果的争论。社会之大,见仁见智,我们生活的空间绝不会纯净得像一片白雪一样晶莹。但正是老师的这篇词从那时候交给了我一种东西—当然他在其后的言行仍在教导着我们这种东西,就是:人,不该只为自我而忘记社会,忘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忘记人民。
这种教育,对于我们这些“无能”的学生,大约是足可以受用一生的了,因为,立于天地之间的堂堂正正的人,是绝不会像动物一样只去筑自己的小巢的,也正因此,我更理解了湖南卫视“恳谈会”上“老三届”们的无悔和他们无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