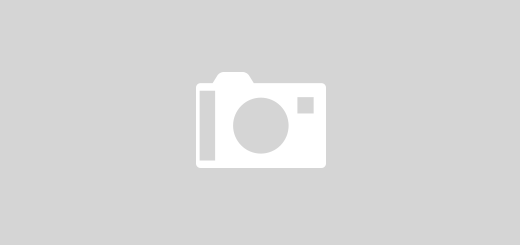电梯爸爸的纯手工爱情
初相识时,她是女孩们都羡慕的白衣天使,而他只是机械厂的一个维修工人。
第一次见面,她走进他们厂里,看到的是满墙贴着打倒他的大字报,但两人还是谈起了恋爱,她说她看到了他的踏实肯干、勤奋努力。
 八个月后,她背着个柳条箱子,里面放着她的衣物,从老家临沭坐公共汽车来到他的住处临沂。两人把各自的被褥放到一起,简单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她说:“只要两人相爱,就是最大的幸福!”
八个月后,她背着个柳条箱子,里面放着她的衣物,从老家临沭坐公共汽车来到他的住处临沂。两人把各自的被褥放到一起,简单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她说:“只要两人相爱,就是最大的幸福!”
结婚后的第十七天,他便响应国家支援三线的号召,踏上了去云南的火车。未曾想,到昆明没几个月,他就患上了一种怪病,四肢绵软,只能说话不能动弹,经过几家医院治疗,最后确诊为“重症肌无力”。
远在山东老家的她听说后,一定要到云南看望丈夫。一个人背上烙饼,从临沭到临沂,从临沂到济南,从济南到昆明,汽车、火车,用了七天七夜,终于走到了丈夫的身边。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他恢复得很快,半年后完全康复。时光流转,一晃到了2000年。他和她都退了休,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老两口没有了任何负担,重新回到了甜蜜的二人世界。可是幸福的道路并没有一帆风顺。结婚第32年,她患了脑中风。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出院后,虽然偏瘫,但可以自己走动。他在楼道楼梯的右侧给她自制了多个扶手,他细心地在上面绑了层布,自己在下面帮着她抬脚,每天上上下下锻炼身体。
白天自不用说,夜里,他时常醒来为她盖被子;她想上厕所,只要轻轻碰碰他,即使刚睡着,他也会马上醒来,抱起体重170斤的她。这样的坚持整整10年,3650多个夜晚。
如果这样的坚持能够持续下去,他也会无限地感谢上苍,可偏偏不幸接踵而来。2008年的一天,上楼梯时她因体力不支猛地坐在了台阶上,这一坐就再也没站起来。
他一人已经无法带她出门,天天闷在家里。天性爱热闹的她情绪不好,饭也吃得很少,有时哭得像泪人一样,甚至还要自杀。他看着难受,心里着急,偷偷躲在角落里哭了一次又一次。有一天,她拉着他的手说:“我以后再也下不去了,谁再陪你出去逛逛啊?”他抱着她,泪水滚滚,发誓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再下去的!”于是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能独自把她带到楼下去……
他看到附近一个工地正在施工,高高的塔吊把一小车水泥轻松地运到了楼上,他突发奇想,自己为什么不造一个类似电梯的东西,把老伴从楼上运下来呢?说干就干,凭借当年修理汽车的经验,他先是画草图,后来又结合想法修改。接下来,就该准备各种工具和用料了。
每天早上照顾好她吃饭以后,他拿着采购清单,逐一购买。为了节约成本,他跑遍了全城所有的五金商店;为了尽快掌握焊接技术,他被电焊火光打了无数次眼睛,手被烫了无数的疤;为了检验电梯的牢固性,他把一千多斤的重物背上背下,直到电梯每次上下都牢固稳定。
工夫不负有心人,数月后,一部凝聚了他心血的电梯终于大功告成。他给电梯刷了层新漆,挂上了鲜红的中国结;她洗了头,穿上新衣服、新鞋,转着轮椅来到电梯口。在按动开关,电梯缓慢而平稳下移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离她上次出门已整整过去了半年之久!
他叫王忠玉,今年70岁,是山东临沂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被网友称为“电梯爸爸”;她叫卓宝兰,今年72岁。她说:“我找了一个好老头子,一直牵手,牵手到永远。今生一块走,下辈子还在一块走。”他笑得憨憨的,“我就是她的腿,会推着轮椅去她要想去的地方。”
简陋的支架、用来挡风的塑料布和长短不一的木板,却载满了爱意与浪漫。爱情可以是一颗钻石,也可以是一部手工打造的电梯。
初相识时,她是女孩子们都羡慕的白衣天使,而他只是机械厂的一个普通维修工人。
第 一次见面,她走进他们厂里,看到的是满墙贴着打倒他的大字报,但两人还是谈起了恋爱,那时的她也许没想过自己会有一见钟情的恋爱,她说她看到了他的踏实肯干、勤奋努力。
一次见面,她走进他们厂里,看到的是满墙贴着打倒他的大字报,但两人还是谈起了恋爱,那时的她也许没想过自己会有一见钟情的恋爱,她说她看到了他的踏实肯干、勤奋努力。
8个月后,他说:“我们结婚吧?”她说:“行。”于是她背着一个柳条箱子,里面放着她的衣物,这是她全部的嫁妆,从老家临沭坐公共汽车来到他的住处临沂;当时他也是家徒四壁,没有家具,没有摆设,两人把各自的被褥放到一起,简单吃了一顿饭,就结了婚。她说:“只要两人相爱,就是最大的幸福!”
1968年,“文革”初期,毛主席号召青年人“支援大三线”,积极上进的他报了名。结婚后的第17天,他便踏上了去云南的火车。但是未曾想,到昆明没几个月,他就患上了一种怪病,四肢绵软,只能说话不能动弹,经过几家医院治疗,最后确诊为“重症肌无力”。
远在山东老家的她听说后,一定要到云南看望丈夫。一个人背上烙饼,从临沂到济南,从济南到昆明,倒汽车、倒火车,用了7天7夜,终于来到了丈夫的身边。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他恢复得很快,半年后病情缓解了。两人从云南返回家乡,开始了平静的小日子。
时光流转,一晃到了2000年。他和她都陆续退休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老两口没有了负担,重新回到了甜蜜的二人世界。那段日子,老两口一起跳舞,一起逛商场,还像年轻人一样补拍了婚纱照,他们的恩爱让邻居们羡慕不已。
可是幸福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结婚第32年,她患了脑中风。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出院后,她虽然偏瘫,但可以自己走动。他在楼道楼梯的右边给她自制了多个扶手,为了不让她磨破手掌,他细心地在上面绑了一层布,自己在下面帮着她抬脚,每天上上下下地锻炼身体。
天热时,他带着她出去散步,看街上人来人往,和老邻居们聊聊天;天冷时,他就在家里的阳台上自制了一圈木制扶手,扶着她绕着阳台走,直到她累了,想睡午觉。她睡着后的半个小时,是一天24小时中唯一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也只有在这半个小时里,他才能好好坐在沙发上歇一歇,放松自己。他说,给他半个小时,他就能鼓起力气第二天再陪着她走下去。夜里,他时常醒来为她盖被子;她想上厕所,只要轻轻碰碰他,即使睡得很沉,他也会马上醒来,抱起体重170斤的她。这样的坚持整整10年,3650多个夜晚。
如果这样的坚持能够持续下去,他也会无限地感谢上苍,可不幸偏偏再次接踵而来。2008年的一天,她上楼梯时因体力不支猛地坐在了台阶上,这一坐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由于活动量不足和药量的增加,她的体重增加到了180斤,他一个人已经无法带她出门,天天闷在家里。天性爱热闹的她情绪不好,饭也吃得很少,有时哭得像泪人一样,甚至还要自杀。他看着难受心里着急,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了一次又一次。有一天,她拉着他的手说:“我以后再也下不去了,谁再陪你出去逛逛啊?”他抱着她,泪水滚滚,发誓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再下去的!”于是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能独自把她带到楼下去,能让她像以前一样快乐,和街坊邻居聊聊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一天,他到离家几站路远的一个农贸市场买菜,远远的,他看到附近一个工地正在施工,高高的塔吊把一小车水泥轻松地运到了楼上,他突发奇想,自己为什么不造一个类似电梯的东西,把老伴从楼上运下来呢,自己家住在二楼,一楼没有人入住,在楼房连接处造个电梯,把老伴载下去,就省力多了。
说干就干,凭借当年修理汽车的经验,他先是照着塔吊的形状画草图,后来又结合自己的想法修改。经过努力,按照自己设计的草图做出了一个模型,接下来,就该准备各种工具和用料了。
每天早上照顾她吃完饭以后,他就在她的声声叮嘱中出了门,他拿着开好的采购清单,逐一购买。为了节约成本,他跑遍了全城所有的五金商店;为了学会电焊,他给20多岁的焊接师傅倒水点烟,说尽好话;为了尽快掌握焊接技术,他被电焊火光打了无数次眼睛,手被烫了无数的疤;为了检验电梯的牢固性,他把1000多斤的重物背上背下,直到电梯每次上下都牢固稳定。
工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后,一部凝聚了他心血的电梯终于大功告成。他给电梯刷了一层新漆,挂上了鲜红的中国结;她洗了头,穿上新衣服、新鞋,转着轮椅来到电梯口。在按动开关、电梯缓慢而平稳地下移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离她上次出门已整整过去了半年之久!
儿子被老爸老妈的爱情所感动,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组照片,展示了父亲为母亲自制的电梯。网友惊呼“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不用住太豪华的房子,也不用每天开奔驰,只需要对方多一些关怀,多一些爱就足够了。”
他叫王忠玉,今年70岁,是山东临沂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被网友称为“电梯爸爸”;她叫卓宝兰,今年72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她说:“我不会说好话,我很感激他,我找了一个好老头子,一直牵手,牵手到永远。今生一起走,下辈子还在一起走。”他笑得憨憨的:“结婚40多年了,再过几年就金婚了。我就是她的腿,会推着轮椅去她要想去的地方。”
简陋的支架、用来挡风的塑料布和长短不一的木板,却载满了爱意与浪漫,爱情可以是一颗12克拉的钻石,也可以是一部粗糙的手工打造的“电梯”。
很多年后,玲玲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彼得的英国男人在网上问候她的那个下午,那注定是一个神奇的日子,那是2007年4月的某一天,故事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一年,离玲玲从安徽老家念完中专,只身一人来到上海闯荡过去了好几年。当年20岁不到的她口袋里只有220元,跑来上海,在餐厅打工,刷碗洗盘子,她什么都干。业余时间,凭着一股韧劲,她数年坚持自学日语,最终考出了日语一级,这是日语考试里的最高级别,后来她因此在一家日企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她的奋斗历史,而是这个女子的爱情故事。因为爱情同样眷顾着这个勤奋的安徽妹子。四年前,玲玲在网上认识了同样在上海工作的英国人彼得,两人相识相恋、相知相许,如今,他们依然在上海共筑爱的小巢,以婚姻的名义幸福着。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她的奋斗历史,而是这个女子的爱情故事。因为爱情同样眷顾着这个勤奋的安徽妹子。四年前,玲玲在网上认识了同样在上海工作的英国人彼得,两人相识相恋、相知相许,如今,他们依然在上海共筑爱的小巢,以婚姻的名义幸福着。
初识在网络,因日语结缘
那天,玲玲正在上网,突然收到一条日文问候,显得非常突兀,玲玲不由警觉地问:“你为什么加我啊?”对方说:“我好多年没说日语了,想找个人练练,看你名字上的日文字母我刚好都认识,就加了……”玲玲一看资料,是英国人。她在心里想,说日语的英国人啊?没见过!玲玲继续问:“难道你真的只是上网找人练口语吗?”对方的回答很绅士:“真的只是出于单纯的学习目的,你不要误会啊。”
玲玲还是相信彼得了,并且发现英国绅士的日语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多了!聊到第三天,彼得便热情地邀请玲玲吃拉面。
在学习日语多年的玲玲看来,会说日语的中国人见过不少,说日语的欧美人还真没见过,很是好奇,外加这个老外给他的感觉有点亲切,所以便爽快答应了。两人相约在静安寺地铁站见面。玲玲在地铁站一边低着头接电话,一边发现一双大脚正往自己的方向移动。玲玲顺着大脚慢慢抬起头,望见一个大个子老外,她嘿嘿笑了两声作为打招呼。玲玲对彼得的第一印象就是:高——186cm的海拔啊;光——当时的彼得是亮亮的光头;眼镜——圆圆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有股子斯文劲儿。
要说起彼得对玲玲的第一印象,那可就是活脱脱一个中国传统妇女的小媳妇儿形象了,这跟后来那个张牙舞爪扯起喉咙都能震倒酒瓶的形象简直是差了个十万八千里啊!眼前的彼得是英国南安普顿人,家有父母、一个律师姐姐、土耳其姐夫和一个学跳舞的妹妹,毕业于布里斯托大学哲学系,爱好摄影,尤其擅长建筑摄影。毕业后离家远走日本,当了一名外教,四年后带着一小笔“巨款”回到英国某摄影学校深造,两年后退学,才来到了上海。
“嗯,交待完毕,那你的呢?”彼得推了推眼镜。“家庭人口跟你一样多,5口人,只不过我有两个弟弟;来自安徽,父母都是农民,混迹上海多年,良民一个;学习劲头应该不输给你,自学日语和英语,嗯哼,说得还不赖吧?”玲玲非常简单介绍了家庭。“自学的?太厉害了!”彼得不由挑起了大拇指。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彼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经过了几次见面吃饭,又经过一次莫干山的骑行活动,爱情的小火苗在两人心中潜滋暗长。中国姑娘并不急于表达,但直白热情的英国绅士却已按捺不住啦。莫干山之行后的一个晚上,玲玲下班到公司楼下,一抬头便看到绅士衬衫笔挺地站在公司大楼正门口,大光头下面娇艳的玫瑰花分外耀眼。时值下班高峰,大楼下来往的人很多,大家都向这个手捧一大束玫瑰的老外投去好奇的目光。玲玲见状,害羞又尴尬,本能地扭头就跑,彼得见状拔腿就在后面追,人高腿长,没三两步便赶上了,一把将玫瑰塞到她怀里,然后站住笑呵呵地看着玲玲。姑娘的脸皮薄啊,脸蛋蹭一下子就通红了,但并没有将玫瑰花推出去,显得既羞涩又甜蜜。一看这么个状况,彼得知道有戏了。
就这样,他们相爱了,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姑娘,用日语谈着恋爱。试想,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街头、在餐厅、在超市、在家中都叽叽呱呱说着日语,会不会有那么几秒,他们自己都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但也正是因为日语这个“共同语言”和同在上海打工的这份惺惺相惜,让两个人的心灵越靠越近。后来,玲玲进修了英语,两人便开始用英语和日语夹杂着交流,现在基本是用英语对话,偶尔开玩笑的时候说日语。不过,每当吵架的时候,情急所致为了“图方便”大家都会使用各自的母语,玲玲更是会用家乡方言,就这么各嚷各的,互相吼个痛快!
后来彼得一直拿这个笑话玲玲:“我从来不知道有你这种女孩!会被玫瑰花吓跑!”
“你不知道中国女孩子很含蓄啊!”
“难道你们中国男孩子没有拿玫瑰花求爱的吗?我喜欢直接表达。”
“受不了你啊……”玲玲白他一眼,看得出来,他们很幸福。
事实证明,英国绅士彼得的确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喜欢直来直去,不懂女朋友的各类暗示。恋爱之初,玲玲的确为此颇费脑筋,无法适应。经过磨合,玲玲很快也学会了直白的表达方式,跨过了沟通这道坎,两人的感情更为深厚了。
无法根治的病,因爱情的力量抵挡病魔
所有的故事都有曲折,玲玲他们的故事有浪漫桥段,自然也有辛酸往事。这天,彼得帮忙整理着玲玲刚搬来的东西,随手翻到厚厚一叠化验单,日期是2004年和2006年。化验单上,血小板上那栏是3000,旁边有一个下降的符号。彼得看不懂中文,但他知道向下的箭头代表低于正常值,便试探地问玲玲:“你以前身体不好吗?”
看到那些化验单,当年对疾病的焦虑和恐惧一齐涌上了玲玲心头:“其实,我早应该告诉你的,我得过血液病……”
玲玲清晰地记得那是2004年12月的一天,一觉醒来,全身上下毫无征兆地布满了针孔状的出血点,吃饭时舌头都在冒血,玲玲吓坏了,直奔医院。医生看了她的报告,让她火速住院,并语气凝重地告诉她,她需要立刻输血小板!正常人的血小板是10-30万,她现在只有3000了!情况很危险!
医生的话把玲玲震住了,她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她一声不吭地来到病房,看到“血液科病房”、“肿瘤血液科”这几个大牌子时,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便嘤嘤地靠在墙上哭了起来,惊动了当班医生和护士。医生告诉她,这个时候最忌情绪激动,会诱发颅内出血,有生命危险!
直到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玲玲的情绪才平静了下来。接下来的一个月,打针、输血、吃药、静养……血小板总算慢慢回到了正常水平。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了很多。玲玲遵医嘱继续吃药,并且默默忍受着激素的侵蚀,使得她的身体不再纤细苗条……
2006年,玲玲本以为病情已经远离,然而病情复发了,去检查,血小板只有8000。尽管她知道这不能激动不能哭,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并且有种绝望和窒息的感觉。又是熟悉的打针、输血、吃药、静养……然后就遇见了彼得。
这是玲玲的心病,有很多次她都想主动告诉彼得,但话到嘴边又开不了口。因为她自己知道,她爱他,担心他为此而离开她。她不能完全确定,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男人,会不会介意这一切。当彼得偶然翻起化验单,玲玲意识到是该坦诚说出这段病史了,就算彼得接受不了,她到也心安了。
“你知道吗,这个病是无法根治的,虽然轻易不会夺走性命,但是会有那么一天,身体对激素不再敏感,抵抗力也因此下降。你会介意吗?”玲玲的声音越来越轻,说完后反倒变得有些许轻松了。
出乎玲玲意料的是,在她看来很纠结的事情,在彼得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阻碍。听完玲玲的诉说,彼得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摇着头笑着说:“怎么会介意呢?我爱的是你,我只要你健康的好好的!”彼得还秀了秀胳膊上的肌肉说,“放心吧!我以后来保护你!病魔看到我这个大块头在你身边,早吓跑啦!”
说来也是幸运,在和彼得相恋结婚的四年时间里,玲玲的病竟没有复发过。这或许是爱的力量吧!
从逼婚到结婚,战胜结婚恐惧症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到了2008年。那天两人正在吃晚饭,突然天空倾盆大雨,玲玲看着灰蒙蒙的窗外,突然觉得无限伤感,已经奔三的人了,还未成家,每年回家父母都会问什么时候结婚?而且也想稳定下来有个家了。
想着想着,玲玲便幽幽地对身边的绅士说了一句,今年过年去我家吧!绅士愣了一下,问了句,为什么?瞬间,玲玲觉得自尊心一下受到了伤害,直视他的眼神也变得犀利冷峻。彼得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过于严肃的气氛,埋头拼命吃饭。玲玲不依不饶,一字一句道:“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去还是不去?”绅士放下碗筷,正视着玲玲,脸上带着一丝不悦:“为什么这么急呢?我会跑掉吗?我们不能多点了解吗?”
玲玲一下子急了,大声地告诉他,“我已经很了解你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体贴真爱我的好男人,跟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很开心很快乐,过去的一年零二个月根本不够,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这句话显然让彼得很受用,他拉起玲玲的手,含情脉脉地说:“我也爱你,我也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
但玲玲看得出彼得的犹豫不决,尽管他不悦的情绪只闪现了那么一会儿,还是被玲玲捕捉到了,她感觉得出,彼得对婚姻似乎有一点恐惧和排斥,至少不像她这样充满向往和迫不及待。她决定好好和彼得谈一谈,用西方人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谈,遮遮掩掩总是解决不了问题。
果然,如玲玲所料,谈话中彼得透露出一些不同的想法,他首先担心玲玲以后到国外生活不习惯。彼得列举了他在各个国家遇到的许多困难和痛苦。对于这点,玲玲嗤之以鼻,想当年她19岁怀里揣着220元孤身一人闯上海滩,难度绝不比去国外生活难,再说她的外语水平绰绰有余。第二个担心让玲玲哭笑不得——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是未雨绸缪吗?连婚都没结,就担心孩子教育的问题来了?玲玲直接问彼得,你觉得我素质怎么样?难不成你还担心我把孩子教得比自己还差?第三,彼得担心玲玲婚后性格大变。他列举了很多他同事老婆的极端例子,变成了母老虎。玲玲忍不住大笑说:“我能变到哪里去?我现在已经够凶了,要变只能变好,变温柔!”尽管玲玲已经表现得足够大方,但彼得似乎还有些优柔寡断。在玲玲的追问下,彼得终于说出了最后的忧虑,他说他来自一个传统的英国家庭,对婚姻有着传统的观念——一结婚就不能轻易离婚,所以他需要谨慎,以确定自己和对方都能够对婚姻保持忠诚。
听完彼得的话,玲玲整理一下思绪说:“谈恋爱的甜蜜虽未必会延续到婚姻里,我也不知道你婚后会不会脾气性情大变!我也不能保证不会变得暴躁!我也承认,我们在不少地方有文化差异,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可能就放弃去争取幸福,我们的感情明明就是越来越好的,明明已经适合结婚了。”
中国姑娘的真诚打动了彼得。两个人先是盘算着见家长、登记,再考虑办婚礼。有一天,玲玲下班回家时发现灯是关着的,但屋顶的吊灯上吊着一只开着的手电筒,心想这人在搞什么鬼啊!顺着手电筒的光看到床上有个小盒子,玲玲狐疑地把灯打开了,一分钟不到又关了。玲玲的第六感总算察觉到一些端倪,她径直走到盒子边,看到橘红色的盒子外面露了一截彩带,上面用黑色水笔写着“pull(拉)”,下面还画了一个朝下的指示箭头,玲玲摸索着把彩带拽了出来,彩带上的黑色水笔字也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天哪!原来是“will you marry me?(你愿意嫁给我吗?)”原来这就是精心策划的求婚仪式!
玲玲随即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枚小小的钻戒,虽然小,却也闪烁着光辉。玲玲只觉得自己的泪光和钻石的光芒交汇在一起,在迷离的视线中,久候于阳台上的彼得闪亮登场了,只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拿着一瓶香槟和两个杯子走到玲玲身旁,举着戒指半跪在玲玲身边柔声的问道:“你愿意嫁给我吗?”此刻的玲玲已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只顾流泪和点头。
2008年12月,两人登记结婚,后来在上海见了彼得的家人。婚礼是在玲玲老家办的,彼得说还欠玲玲一个在英国的盛大婚礼,但由于两人一直生活在上海,忙于事业,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就让这个美丽的期待先持续一会儿吧。
圆梦共创业,嫁你就要追随你
再美丽的跨国恋,再童话般的爱情剧桥段,最终也都会回归到柴米油盐的琐碎上。彼得在上海的这些年一直在国际学校做着外教。作为老师,他是一个尽职得不能再尽职的好教师,但是做教师清贫的收入也让绅士做了一名“月光族”。
这些年,彼得利用业余时间也接过大大小小不少建筑项目,拍摄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他对摄影艺术的痴迷也深深感染着玲玲,他会在大冬天的凌晨起床背上相机,转几趟地铁去郊区蹲守一天,只为拍一个楼,他认为好的建筑的都是有灵魂的,他要把镜头对准这些静谧的灵魂,捕捉他们与天地交融的美。接一个摄影项目的确收入可观,但是考虑到摄影师工作的不安定性,彼得一直没有放下全职工作。
其实,彼得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做一名专职的建筑摄影师,这也是他来上海的初衷。他是个在建筑摄影方面十分有天赋和抱着极大热情的人。今年6月的一天,彼得回家对玲玲说,他不想再做老师了,还列举了一大堆理由,比如赚得不多、不能很好地照顾玲玲、不喜欢学校的氛围等等。玲玲马上就知道了彼得的心思,因为彼得曾经很坚定地告诉过她:“我想做全职的建筑摄影师。”她一直记得。
但是,那一晚玲玲没有急于表态,她一个人安静地想了很多很多。她发现自己越是年近30越是不如20岁不到时那般敢闯敢拼,现在是越发地畏手畏脚、患得患失。她知道,做全职摄影师的愿望已经在彼得心中埋藏了太久太久,他也为此准备了很多年。玲玲很清楚,他需要她的支持,但她自己似乎又下不了决心去辞掉优渥的工作。转辗反侧一晚后,玲玲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一早,玲玲便给之前通过面试的某知名日企打去了电话,说了好多个对不起,说自己不准备找工作,说她要和老公一起创业了。
对玲玲的理解和追随,彼得心存感激。就这样,2011年9月,夫妇俩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上海洛唐(建筑)摄影有限公司。对他们来说,新的生活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