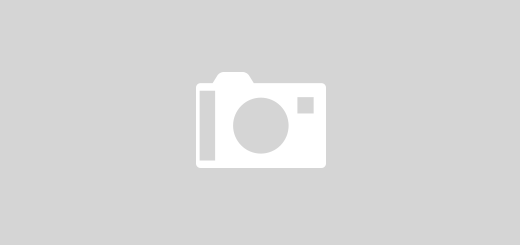66年藏了一份爱情
他是个黑人老头,她是个白人老太。他和她,坐在花坛边。澳大利亚春末的明媚阳光,将他们身后悉尼Blacktown(黑人聚居区)的老人院两层小楼的影子拉得很长。离他们十步开外,我就清楚地看到,他在说着什么,嘴巴不停地动,她的眼角,还有嘴角,挤满了笑。
 我微微倾身,说:“我叫Leo,新来的义工。我能分享你们的快乐吗?”老太没有反对,老头看着我,轻轻点头,“我在讲述我对她66年的爱,你愿意听吗?”
我微微倾身,说:“我叫Leo,新来的义工。我能分享你们的快乐吗?”老太没有反对,老头看着我,轻轻点头,“我在讲述我对她66年的爱,你愿意听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安安静静搬来一把椅子,正对着他和她,坐好。
“我是苏丹人,1940年坐船到澳大利亚,最初的落脚地是塔斯马尼亚岛。很巧,我住的出租房旁边就是汉娜的家……”兴致勃勃讲故事的老头忽然踩了刹车,他挠挠后脑勺,面呈歉意,“我忘了介绍我们的名字了。我叫约书亚,她叫汉娜。”
“从到塔斯马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认识汉娜了。可是,她不认识我。那时,我只有13岁,和我的爸爸、叔叔住在一起。汉娜比我大一岁。那时汉娜正在学骑自行车,她骑不好,老摔在草地上,可她从没哭过,每一次,我都听到她咯咯地笑,然后爬起来,扶起自行车继续骑
“汉娜从没发现过我。我总是躲在树后,伸出脑袋,悄悄看。我知道,我是黑人。而汉娜,白白净净,眼睛又大又圆。她的头发金黄金黄,好长,风一吹,长头发在风里荡来荡去,你能想到的,那有多么美!”
“她是天使,而我是黑人,我怕我从树后面走出来,会吓坏汉娜。只用了6天,汉娜学会骑车了。她飞快地踩着自行车,像一阵风卷过去。我仍旧躲在树后,痴痴地望。一个人时,偷偷地,我对着树洞一遍又一遍说:‘汉娜,我爱你。’”
汉娜16岁那年,他们全家搬去墨尔本。我对坚持留在塔斯马尼亚岛谋生的爸爸和叔叔说,我已经长大了,应当自己出去闯天下。不顾他们的坚决反对,我只身来到墨尔本。我不知道汉娜住在哪儿,可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能够找到她。
“后来,我进了一家鞋店做工,那时,我已满16岁。我暗想,汉娜那么美,她肯定和其他漂亮女孩一样喜欢打扮,那么她总有一天会来的。有天早上,我刚上班,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了鞋店。天啊,我快要晕过去了,那正是我日思夜想的汉娜!可是我很快又急得要哭出声来,因为,汉娜的手紧紧地挽着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哦,汉娜,她恋爱了!
“汉娜再没来过鞋店,可我终于找到她的家了。每天下班后,我从鞋店出发,走过三条街,穿过一个小花园,去汉娜家的对面望望。我每次都数步子,一步,一步,一其有797步。当然,也不是固定的,有时是789步,最多时走811步,我就看到汉娜的家了。偶尔,我能见到汉娜站在家门口张望,她在等男朋友。有时,不见她人,但可以听到她在屋子里笑。更多时候,我看不到汉娜的身影,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我就在她家门口站一会儿,再转身往回走,走回鞋店,上小阁楼吃饭睡觉。
后来,汉娜结婚了,换了新家。我不清楚从鞋店走路去汉娜的新家有多少步,但我清楚,开车去那儿需要12分钟。不是每天,但是经常,我会开车去看汉娜。我将车远远停下,透过车窗,目光越过低矮的木围栏,看到汉娜和她的丈夫在花园里浇水、谈笑。很快,一个小女孩加入了汉娜和她丈夫的欢乐队伍,那是他们的孩子。我敢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天使。我很奇怪,我心底早已没有了被锋利的刀子一下一下割裂的感觉,酸楚也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欣慰和情不自禁的欢喜。每每看到汉娜一家三口,甜甜蜜蜜地在一起游戏欢笑,我都由衷地感到愉悦。
知道汉娜的丈夫和孩子去了天堂,很偶然,也很突然。因为父亲病重,我回塔斯马尼亚住了两个星期。回到墨尔本,我赶去参加一个朋友母亲的葬礼。在墓地,却意外地看到了汉娜。可怜的汉娜,一脸悲戚。我的心,顷刻间碎成了玻璃屑。
约书亚抬起右手擦拭眼睛,才继续故事的后半部分汉娜的丈夫开车载着全家出去度周末,出了车祸。汉娜受了伤,而她的丈夫和孩子因失血过多去世了……
我辞了鞋店的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和朋友合开了一家蔬果店,从那儿走路去汉娜家只要一分钟。我们的蔬果店生意持续了26年。这26年里,我没有结婚,汉娜也没有再婚。不知道是汉娜自己不愿再当一回新娘,还是没人愿意娶她。而我,自始至终,从没向汉娜求过爱,理由只有一个她是天使,而我什么都不是。26年里,我以义工的身份,每周两次出现在汉娜面前,开开心心陪她说话,替她照料花园里的花草,采购生活用品。
26年过去了,我将自己的股份全部卖给了蔬果店的合伙人。因为,汉娜要搬到悉尼来,我也就悄悄地追随着她来到悉尼。在悉尼的温雅,我开始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我都能见到汉娜。因为我们租住的房间门对门,一开门,就见面了。汉娜信仰主,她每个周末都去教会。我最初只是跟着她去,后来我也信了耶稣,而且很快成了教会最热诚的福音干事
“我们来到Blacktown是6年前的事。来这里,是我的主意。因为这儿有太多我认识的、要好的黑人兄弟姐妹,我想向他们传福音。”讲到这里,约书亚忽然转身偷偷乐起来,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你能猜到吗,我对汉娜说,我们到Blacktown传福音去吧。她居然连一秒钟都没犹豫,就和我一起来了。直到两年前,我们老了,住进这家老人院。你相信吗,她一直不知道我是她当年在塔斯马尼亚的邻居,曾悄悄躲在树后看她学骑自行车,也不知道我是她住在墨尔本时,一直坚持帮助她的义工和邻居:更不知道我是在追随她来到温雅,并想方设法租住在她门对门的房子的人她惟一清楚的是,我和她一样,都是信了主的肢体。”
我张口结舌。
约书亚觉察到了我的疑惑,他再一次得意地乐了。他用嘴角示意我去看汉娜的眼睛。汉娜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老花镜。坦白说,我看不出异样,我只留意到汉娜满脸的笑容,在暖暖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馨。
“在那次车祸中,她虽然没有丧失生命,但却从此失去了光明。她美丽的大眼睛还在,但眼前只有混沌和黑暗。她的光明,亮在心里。”约书亚说。
我恍然大悟:“她失明了,但是可以聆听。她一定是因为听了你给她讲述几十年的爱慕,而倍感甜美,因此满脸尽是春色。”
没料到,约书亚居然摇头:“不,还是因为那次车祸,汉娜的听力严重受损。前些年,她还能凭助听器勉强听到一些声音,近几年,则完全与声音绝缘了一”
我满心疑惑又全部跑到脸上来了,我结结巴巴地问“可是,我明明看到,她一边听你讲故事,一边面露微笑。”
“她用手来聆听。”约书亚说。此时,我才注意到,两位老人的手,轻轻地,又是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双手,黑白分明的手,安静地搁在老头的左膝上。
打量着他和她握在一起的手——真的,这和谐甜美、温馨平静的一幕很让我着迷。我都看得痴了。我想我不会猜错,凭着紧握的手,失明失聪的汉娜知道,有~颗心,和她靠得很近,凭着紧握的手,无儿无女的约书亚知道,有一颗心,在认真聆听他讲述自己深藏在心底66年的爱。
那时候,他是文章里写的那种“最后一个去食堂”的男生。因为他穷,最后一个去,可以只要两个馒头,偶尔要一份廉价的菜,而不用去承受同学诧异或同情的目光。
没错,贫穷。贫穷是他从小到大对生活的全部概念。改变贫穷,便成了他刻苦读书的动力。
 半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这所著名的学府,父亲送他到车站,含泪塞给他的那把钱,交够一学期学费后便所剩无几。他从此开始在半饥饿状态下一边学习一边度日,周末做家教,积攒新学年的学费。
半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这所著名的学府,父亲送他到车站,含泪塞给他的那把钱,交够一学期学费后便所剩无几。他从此开始在半饥饿状态下一边学习一边度日,周末做家教,积攒新学年的学费。
他从来没有吃过早饭,午饭和晚饭内容雷同。两个馒头,一份成菜或是因为剩下而减价的菜……
他消瘦,却挺拔英俊,贫穷却成绩优异,拿最高额的奖学金,并且从不抱怨。
她慢慢喜欢上了他,那个沉默而优秀的男生。
她不是优越家庭中的女孩,父母都是县城小工厂的职工,大学费用,对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巨大开销。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也选择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常常和室友一起,去商场给某些商品做促销。
喜欢他的时候,她刚给一经营麦片的公司签了合约,周末两天,在一家大型超市促销那种小包装麦片。其中,有一部分是赠品,顾客买够一定数量,就可以获取几小袋赠送的麦片。
那个周末的早上,她去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了他。他是去做家教,那么早,脚步匆匆,只是为了省去坐公交的一元钱。那样消瘦的背影,令她心疼。
那天,她总是想着他,一边热情招呼顾客,一边想起他消瘦的背影。然后,看着堆在一旁做赠品的麦片,她突然动了心思。
那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她把那些没有赠完的很多小包装麦片装进了自己的大背包……除了正常商品,赠品的领取和返回没有确切的记录。她决定把那些麦片偷偷带回去,送给他。虽然他不曾倾诉和抱怨生活的苦,可是一个动了情思的女子的敏感,还是让她轻易觉察出了他生活贫穷的真相。
她想帮他,又怕触到他的自尊心,一直不如道该怎么办,现在,她终于有办法了。
周一的下午,她坐在食堂的角落等待着,终于,等到所有同学都吃完饭离开后,他走了进来,照例,两个馒头,这次,连咸菜都没有要。她也买了饭,也是两个馒头,一份咸菜,装着巧遇走到他旁边喊了他一声。
他还是脸红了,她装作看不出来,坐下来,低头吃饭。没有问他为什么只吃馒头,好像没有发觉,好像一切正常。
她装得很好,他的表情也恢复了寻常,低头吃饭,同样很随意的,她把咸菜夹了一块递给他:“太咸了,吃不完。”他一愣,但没有拒绝,掰开馒头把成菜放进去,一大口,吃掉了小半个。
他先吃完了,依旧不吭声,站起来要走。她喊住了他,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的口气,“对了,我今天带回来一些麦片,太多了,给你一些吧。”
他似乎没听明白,回过头来看着她。她俏皮地笑“是促销产品的赠品,根本送不完,都让我背回来了。我也不爱喝麦片,你帮我解决一部分吧,可以当早餐。”
他还是没有说话,习惯的沉默,分明是拒绝。
她索性撒娇了“那么重,下周我还得背到超市,送不完,又背回来,多麻烦啊,时间长了还变质,帮帮忙哦……”然后嘴巴嘟了起来。
他不由笑了,她的样子真可爱。她没有大城市女孩的优越傲气,也不像农村来的女孩那样心思敏感一只是生活贫困的他却不敢向这个可爱的女孩靠近半步。但是这一刻,他,如何拒绝这样表情的她?
看他笑,她赶快站起来,把早已装好的麦片从包里拿了出来,一把塞到他手里,然后扭头就跑了。
她终于把麦片给他了,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偷偷地笑了。
以后,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把这些小袋的麦片送给他做早餐。她知道对他来说一小袋麦片绝对吃不饱,可是麦片里有牛奶和白糖,至少能增加一部分营养。
就这样,过了半年,那天,她突然又照例掏出已准备好的麦片给他的时候,他突然握住她的手说“以后,我一定让你过最好的生活,一辈子,对你好。”
之前,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更不用说爱。她不敢说,怕他拒绝,甚至不敢让他去感觉到。而此时,他的一句话,直白直接,不仅是认可,更有不容置疑的承诺。
因为激动,她哭了。只是她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敢爱了。她不知道那一天他无意在她的室友那里得知,因为总是“贪污”赠品,那家公司早把她辞退了。后来她送他的麦片,都是她用自己生活费中省出来的钱买的,然后又做赠品送给他。她这样做,只是小心去维护他一直在贫困中挣扎的自尊。
那天,他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号啕大哭。他终于知道,他直在最贫穷的日子里拥有最富有的爱情。所以,他要用心接受她对他的好,她对他的爱。不仅接受,他还要努力回报。这,才是他作为男子汉该做的,而不是逃避和装做不知。
爱你的春光明媚的人无论有多少,已往矣;爱上你风卷残荷的,一人足矣。
 1916年11月8日,患喉结核的蔡锷将军在日本病逝,年仅34岁。
1916年11月8日,患喉结核的蔡锷将军在日本病逝,年仅34岁。
小凤仙得知此讯,痛不欲生。高山流水觅知音,他是她人生最大的亮色,谁知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他就如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永远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这让她怎么面对以后的漫漫人生呢?
在蔡锷的追悼会上送上“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千秋”的挽联后,小凤仙悄然离开了八大胡同。
此后她颠沛流离,嫁过一位师长,师长战死。为生活所迫,她又跟了一个厨子,住在沈阳市皇姑区寿泉街三胡同的一座平房里。因为丈夫姓陈,四周邻居们都称她“陈娘”。她给自己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张洗非。
陈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他隐约知道她是个不寻常的女人,只是,关于过去,她不说,他便不问。她没有工作,只靠他的一点微薄收入过日子,他们住的北厢房只有狭狭的十平方,家里几乎没有家具,惟一像样的摆设,也就是那只天天上弦叫他起来开工的小闹钟。他总觉得委屈了她。所以,只要她喜欢的,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尽量满足她。
她惟一的爱好就是喝酒,几乎每餐都要喝上两盅,那时,他就会挽起袖子为她弄两个下酒菜,偶尔陪她喝两盅。庸常的生活里因为他的温暖便有了些许滋味。
她惟一的乐趣是听戏。一出戏,她听得如痴如醉,恍如隔世。
对他,对生活,她倒也安之若素。不讲究穿戴,只是爱干净,常常把几件平平常常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在她身上,很与众不同。
她随身有个小包裹,那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位年轻英俊的军官。他问过一次,她淡淡一笑,轻声回答:“是个普通朋友。”
日子风驰电掣地往前赶,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顿。不得已,她做了保姆。
她见了一位故人,那是她与从前生活的惟一一点联系。故人是梅兰芳。
1951年年初,梅兰芳率剧团去朝鲜慰问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途经沈阳演出。她闻讯,很想见见这位昔日在北京的旧相识,并求得他的帮助,遂写了一封信寄给梅。
数日后,她接到梅兰芳邀请相见的回信,兴奋异常,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打扮得像过节一样,去见梅兰芳。
这时,她已年过五十,生活忧患,饱经苍桑,故人相见,一言难尽。
经梅的举荐,她到一家机关学校当了保健员。那是她一生过得最为顺意的日子。她表现得很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只是,她从不对身边人说过她是谁。在所有人眼里,她不过是个普通女子张洗非。
电影《知音》放得街知巷闻时,她也隐在人群里看了一遍。高山流水觅知音,银幕上的那对碧人真的是她和蔡将军吗?旧时光里的恋情泛了黄,仿佛那根本就是另一个人的另一种人生。
她已不大记得小凤仙的生活,华裳美服,琴棋书画,迎来送往。然后星火一样遇到生命里的那个男人。他像一道光,照亮了她的整个生命。然后光灭了,她的生命黯淡下去。
她跟陈姓男人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她不曾真正了解他。她只是用他来逃避自己心里的那段记忆。可是,是他给了她一个家的全部温暖。她是明白女子,她何尝不明白,假使蔡将军活着,他们之间,或者也就是一段佳话,如此而已。
而他,用真心待她。他希望她所有的伤都能在平淡的岁月里不治而愈,一如他做的一粥一饭,平常却养人。
她很庆幸遇到他,他一直陪在她身边,给她最平实的温暖。这便够了,不是吗?
1976年,她终于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以76岁之龄病故。她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是突发性的脑溢血。人们把她抬进医院急诊室,抢救无效。
他颤抖着把那张跟随了她一辈子的照片放在了她的衣袋里。泪水从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流下来。
一辈子,他没对她说过那个爱字。他不是小凤仙或者是改名叫张洗非的女子的知音,但是,有些感情,融进了血液里,比水浓。
那也是爱情。
陪她走完了人生衰败的每一天的人,不是蔡将军,而是他。
爱你的春光明媚的人无论有多少,已往矣;爱上你风卷残荷的,一人足矣。